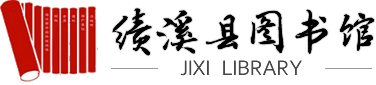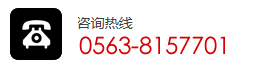“我在讨论晚清的时候,一定会注意到这种先死者的委屈,我会考虑到后死者对故事的描述当中,有没有刻意添加的或者是无意添加一些东西。”
编者按:2017年1月10日,“马勇研究员学术讲座暨荣休座谈会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。期间,马勇谈到了自己晚清史的治学经验。以下为发言全文,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。
关于晚清史研究,我想讲三个问题。
第一,从哪个角度来进入晚清;第二,要注意到失败者的记录;第三,从全球史和现代化的角度,来谈谈我对晚清史的思考。
从清朝遗民的角度进入晚清
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之前,不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学者,对晚清史已经有基本的政治框架建构,我们想有一个大的突破可能非常难。当然如果没有突破,也不能照抄前辈的东西。在20多年的时间里,我就想能不能够重新建构一个晚清史的叙述框架。做历史的时候,强调历史一定有一个终极的真相,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,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,各个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
过去可能比较倾向于革命史的研究,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和海外,最近两年我更多地倾向于认为,海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,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学者的观念。中国学者在过去关于晚清史的表达,问题在哪?从革命史进入晚清研究的问题在哪?后来我想,可能我们忽略了清朝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。
我最初进入晚清,是从晚清遗民的角度。我在1991年写过几篇关于严复对近代中国问题思考的文章。从严复的观察开始进入晚清,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对晚清的看法。去年我还讨论孙中山,讨论孙中山的时候,我的价值坐标不是革命层面,而是从一个清朝遗民的角度,回到当时的场景下。
清朝遗民的价值观对我影响很大。比如说我多年前写过关于晚清科举改革,科举制度最终的废除,我的分析和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很不一样。一般认为,科举制度就是新教育和旧教育之间的问题,严复在1895年之后,关于科举制度的思考,他不是讲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发生,他实际讲的就是中国的新教育,怎么能重新发现。科举和旧教育和新教育并没有多少关联。
我就仔细读严复关于科举问题的讨论,探讨科举制在晚清变革当中的演化,到了甲午战争之后,为什么科举制改革最终走上这么一个结局。从严复的视角,还可以看到他对于晚清制度、政治改革的一些看法。晚清政治转型当中的政治改革,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应有之义,在这个应有之义当中,无论朝野各界,都有自己的一个寻找自己的正当性的判断。严复从晚清到辛亥前后,在学术和政治的关联上做了深度介入。我很多的价值观可能是从他这里引发出来的。
我对晚清的一些史实的判断,还受到另外一个遗民辜鸿铭的影响。我写过几篇关于慈禧太后的文章发表在《南方周末》,引起不少争议。实际上写慈禧太后时,主要的思考,就是多年前辜鸿铭的判断。我们原来看晚清皇宫内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冲突,慈禧太后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形象。但是去读辜鸿铭的资料的时候,就会感觉到完全不一样。当然我不会完全相信辜鸿铭的判断都是对的,黄兴涛教授多年前就把他估价为一个文化怪杰。因此,我在通过辜鸿铭理解晚清的时候,可能会把他的观点过滤了一下,但是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,一个思考的视野,在这个视野里面,可能我们能够很宽容的,能够带着敬意去理解晚清的政治领导人,他们思考国家前途,在变化和转型之间究竟如何选择。
很多做研究的人都认为《清实录》不应作为重要的史料出处,但《清实录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它的价值观。我参加《清实录》委员会第一次大规模讨论,当时提出,我们新编清史,要回到王朝本位。我们一定要以一种王朝的立场,王朝的意识来看待清朝的历史,才不会在整个清朝历史当中打架。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价值观,一个校正。
当然,进入晚清讨论的时候,我不完全从革命史观相反的立场进入,而是从清朝人本身的看法进入。清朝的遗民到民国时期,他的价值立场变得比较反动,但是回到晚清的场景下,它的价值观可能比较中立。因为他们既不是清末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,也不是纯粹站在革命党一边,从反对和批判的立场去思考。
警惕后死者的话语霸权
一般的历史学者都会有这么一种警觉和自觉,就是历史是胜利者建构的,一个研究者要对这个胜利者的话语有非常高的警惕性,不管胜利者书写历史是真的假的。
这些年来,我读了很多回忆录,最深的感受,就是后死者的话语霸权。我竭力支持、推动着口述史的研究,就是因为人人都做口述史,才能鉴别历史的真假。如果不是人人都做口述史,那就可能让后死者形成话语霸权。所以我在讨论晚清的时候,一定会注意到这种先死者的委屈,我会考虑到后死者对故事的描述当中,有没有刻意添加的或者是无意添加一些东西。
比如戊戌六君子和康梁,我在做戊戌研究的时候,思考的就是康梁叙事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。六君子在1898年的9月份政变当中都遇难了。是不是康有为、梁启超描述的就是六君子想的呢?在多年来的阅读当中,越来越感觉到好像不是。这些年,茅海建做了大量的考据研究,我们现在可以更明白地看到,康梁作为后死者的话语霸权。如果从这样一个层面再去进入,再去思考当时的历史场景,思考六君子和其他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关联,可能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看法。
像这种类似的事情晚清还很多。比如两宫之间的冲突,以及慈禧和光绪的死亡,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感觉到,可能后来的研究中,添加上去的故事多于事实本身。因为逝者没法再说话,没法再表达,没法做出任何辩解。类似的事情在晚清史的研究当中,李鸿章、袁世凯等都是。
从全球史关照中国
近代的变革要放在全球史的背景当中去讨论,在这个背景当中,我比较看重的问题,就是西方因素的发生。到十六世纪的时候,其实西方和中国有交往,大致都在仰视中国。西方对中国的仰视,大概持续到了十八世纪,当我们看到孟德斯鸠等人资料的时候,你会感觉到,西方人当时对中国的评价其实相当高。
中国在农业国的状态下,它的政治架构上,在王权体制下,给中国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架构,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概念叫超稳定架构,这可能是对于中国农业国民描述的最高赞美。这种赞美表明当时中国的体制,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的时候,可能不会引发本身的根本性变革。后来还是因为十五世纪之后,西方产生了一个新的元素,这种因素确实是颠覆了近代中国,一直持续到今天。
中国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接纳,让印度文明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,用了八百年的时间。佛教文明进入中国,从东汉初年的冲突,南北朝时期中国成为一个佛教国,但是它真正融入到中国知识阶层、朝野各界或是家庭,大概是在北宋时期,全部进入用了八百年时间。
讨论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过程,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。这个中心问题,我觉得是西方因素的进入。如同佛教文化的进入一样,中国一开始不适应,以乾嘉汉学为例,它对西学是拒斥的状态,但是实际上乾嘉汉学内部对西方科学方法的吸纳,很值得我们今天注意。
到18世纪,西方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,中国就没有像日本的某一些藩国,能够有效让中国的变化和西方处于同步共振的状态,鸦片战争之前、十八世纪早期,中国没有和西方处在一个共振之中,导致后来的问题复杂化。比如,从洋务一直到甲午,只是一种片面的发展,没有整体性的变革,它给后来留下了无穷多的问题。严复当年考虑了一下,就说牛有牛之体,马有马之用,你会觉得,在洋务新政这个时间段,当时的中国人在急切的心态下,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。于是,中国就发展科学技术,在1860到1890年代,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。
但是有一个大问题,比如说教育,如果在1860年,中国当时不是搞科举制的改革,而是和1890年和1901年一样,完全冲破新教育,大概中国就可以避免后来这种状况。为什么在1860年代中国转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,选择学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体性的学习?像郑观应、马建忠,在这三十年当中,断断续续有很多的批评,但是,都是留待于甲午之后,进入维新时代,才能进行真正和彻底的反省。这种做法给晚清最后二十年的变革积累了很多的问题。
变革起于新阶级的诞生
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现代化。中国能不能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,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,能不能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。从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之后,中国在这方面有了很多的发展,国际资本大幅度进入,中国新阶级逐渐产生。1895年之后,中国社会迅速与国际社会建立一种逐渐平等的交流,让自己走向世界。从这个层面去看的话,我想我们可能对晚清的历史主题就更容易理解——晚清的历史主题,从原来经济的变革往政治转型,就成为一个历史的逻辑。
这个历史转型,当然遇到很大的问题。在1895年之后,全国各地的自治运动,包括湖南的发展,都出现了很好的势头。但是突然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,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。如果把这些事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,放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中,关于义和团产生,我的想法就和原来的看法不一样。我认为,义和团是工业化急剧发展当中被甩掉的一波人。
我分析义和团的构成,就没有像上一辈的学者,完全从秘密教会的角度去考虑,我更愿意从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来看——这一波人是急剧工业化过程中,被甩落的一个群体。当然,它获得曝光的一个形式,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秘密组织。过去把义和团看做反帝爱国,我觉得可能值得重新讨论。但是这几年,有人说义和团反人类,我认为更是不对的,我们应该把义和团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中来看。
在中国急剧的工业化,以及衍生的政治变革当中,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一个新阶级诞生之后,对于中国的制度要求。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中期,中国政治变革的呼声高涨。我们去分析张謇这一代先富阶级,可能在1896年,就是刚刚维新一两年的时候,他们实际思考的就是,中国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、资产阶级,必须寻求一种制度保障。
从这个逻辑出发,1898年政治变革的需求,1900年政治变革的需求,都能找到相互之间的关联。从晚清的政治变革,一直到了1908年之后,应该说是可以稳固推进,但是最大的问题在1908年突然出现了,两宫(慈禧、光绪)相继死亡,这可能是晚清政治变革的一个巨大转折,但并不意味着晚清政治变革就必然走向失败。几年前我在讨论保路运动,讨论南北妥协的时候,就觉得这里面可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,从最初放弃帝制走向共和,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趋势,走出帝制完全是一个偶然。因为从1900年从梁启超开始讨论中国体制应该走向什么样的目标,一直到1905年,1906年之后的讨论,当时除了革命党之外,大概朝野各界更认同君主立宪的架构。但因为某种偶然的因素,君主立宪成为被废除的方案,共和体制出来了——这是在南北之间妥协的时候,非常偶然的选择。
章太炎1921年在一篇文章里面说,当时的中国人选择太急切,因为找不到方向,就回到了共和的大一统。这样来讲的话,我们可以看到,为什么在民国初年,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帝制复辟思潮和复辟运动。
清帝国在1912年终结了,但是我们在探讨民国初年政治架构的时候还得看到,在民初的政治架构中,一方面废除了清帝国政治架构大框架,但是其遗留也隐含在很多制度的细节上,民国没有完全把这个彻底斩断。民初的政治架构,从清朝的变革中所吸收的东西,还是相当多。